拒绝标签化是70后作家的唯一标签:“夹缝中的一代”已成长为文坛主力军
时间:2019-11-10 08:53:14 热度:37.1℃ 作者:网络

▶马笑泉。
再过51天,2020年,一个新的时代又来临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或者,在大众读者的视野里,文坛的主角还是有资历、有地位的60后,有读者、有商业价值的80后,那么70后呢?他们似乎处在一个被忽视的尴尬地位。
有人说70后作家是不幸的群体,当批评界和媒体的注意力还在60后作家那里时,80后作家成为耀眼的文化和出版现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70后被一略而过。
可即使在如此尴尬的处境下,70后作家依然试图突出重围,他们以自身的生活经历汇集,以共有的审美体验聚合,竭尽全力进入当下。
如今,中国第一批70后作家已经50岁了,最年轻的,也进入了不惑之年。这个“夹缝中的一代”已经成长为新世纪中国文坛主力军,他们终将也已经开始挑起中国文坛的大梁。
撰文/记者储文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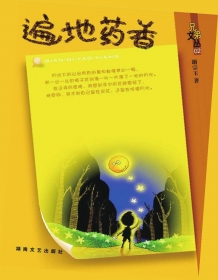
马笑泉:谈起15岁就会血脉偾张
2001年,23岁的马笑泉用钢笔在稿纸上写下《愤怒青年》的第一句话:“我叫楚小龙,吃了难饭的。”写下这一句,热血沸腾。
楚小龙是马笑泉中篇小说《愤怒青年》里的主人公。楚小龙在道上很有名,年轻一辈中,讲狠,没有人比得他赢。如果你跟一个人有仇,或者干脆是看不惯,你可以请他修理修理。但他有他的原则:他要修理的对象必须是罪有应得。他不怕冷。冬天常光着膀子,用雪擦身。15岁时他就这么干,15岁时他的身体里面有把火。
彼时,身为人民银行武冈支行一名普通职员的马笑泉,每天早晨七点半去单位食堂吃早餐,上班,下班后跟同事朋友出去聚餐、玩乐。他像每一个普通城镇青年一样,享受着初涉社会的洒脱和自由。
但楚小龙的存在,让马笑泉的生活又跟普通的银行职员有一些不一样。他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用冷水洗把脸后,就开始用笔和稿纸写作,一直写到七点半去吃早餐。这些零碎而又持续的写作时间,让马笑泉一直保留和回味着15岁时的激情、热血和对英雄主义的梦想。
马笑泉1978年出生于邵阳隆回,陪伴他这一代人成长的,是《霍元甲》、《古惑仔》、金庸小说和港台武侠片。在那样的小县城里,学校附近总有一些无所事事的社会青年,处于放养状态的马笑泉也有机会与这些社会青年交往。他看他们戴露指手套跳霹雳舞,看他们在拥挤的街道上放双手骑单车,看他们动作虽不规范但技术相当精准地“一杆清”打台球,看他们在资江边的城乡结合部里赌钱和武斗。甚至亲眼见到被称作“大角”的帮派大哥因为讲义气替人出头被短铳瞄准仍面不改色,最终倒在血泊中丧命的情景。
20多年后,已是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马笑泉,坐在省作协的茶水间与记者对话时,回忆起自己15岁,依旧心神激荡、血脉偾张。那些以义气为上、以热血为上的“大角”们,依旧是马笑泉心中的英雄。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愤怒青年’,只是因为秉性和境遇的不同,结局也并不同。我看清了他们的困境,却无法伸过手去,把他们从中拽出,唯有怀着同情之理解,从他们的行为和命运进入他们的内心。有时我感觉是他们在借我的手写出各自的命运和心声,有时我感觉他们即我,我即他们。”马笑泉说。
或许不止是金庸等武侠小说在马笑泉的成长中留下痕迹,马笑泉作品中留下的古典文学的语言功底,可以见出从《史记·刺客列传》至《水浒传》的影子。
在文学评论家、中南大学教授聂茂看来,马笑泉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文化是另一种展现暴力之美的表达方式。“从古典文化中汲取文学创作的养料,灌注于新时期小说的创作中,以陌生化的言语效果和情节安排呈现动荡文革的时代气息和对人性造成的精神阴影,这无疑是创新之举。”聂茂说。
在银行工作了八年的马笑泉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单位档案,面对档案上极度扁平干枯的文字,马笑泉当时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虚构一个单位,用小说的形式来为单位里的每个职工建立一份档案,它将比任何官方档案更能体现人的真实存在。这便是《银行档案》。
后来,马笑泉将稿子作为自然来稿寄给中国顶级文学刊物《收获》,没想到一个月之内就接到编辑王继军先生的电话,他表示会马上送审。“其实越是好的刊物,就越不讲关系,只认作品。不然我们这种基层的作者怎么出得来。”马笑泉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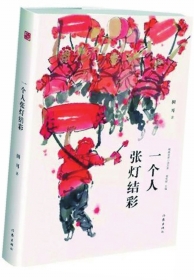
“文学湘军五少将”:湖南70后作家首次集结
“越是好的刊物,越是只认作品。”哪里都一样。
2005年,在颜家文、刘恪、田爱民的策划下,湖南文艺出版社主办的《芙蓉》杂志连续发表了湖南新一代作家的作品,作为对新锐的扶持,当时挑选的作家均为70年代以后出生,崭露头角,在文学期刊上发表过反响较好的作品,或者获过重要的文学奖项。最终,杂志社从当时湖南众多青年作家中有选择地挑出了五位小说作者,并在《芙蓉》刊物上设置了“新湘军”专栏,包括田耳、马笑泉、谢宗玉、于怀岸、沈念等五人,后来,这五人被称为“文学湘军五少将”。可以说,那是湖南70后作家的首次集结。
湘军,少将,这是一个非常有气魄和感染力的称谓。与人们想象中的小团体不一样,马笑泉称,因为各自有不同的写作路径和美学追求,被一同列为“五少将”的五位作家,基本上仍是各干各的活,并未凑成一个流派。
“对世界的疏离和对自我的回归,造就了70后作家创作中的漂泊感,他们的作品既无太多的集体意识,也没有沉重的历史记忆,而是直面个体的日常生活,自觉关注自身的成长记忆。”正如张丽军在《未完成的审美断裂:中国70后作家群研究》中所阐述的,从个人、到时代、到历史,70后作家执着的追问和寻找,是整整一代人的怀旧情绪的精神突围。
“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尽管感到每位作家的风格和个性有很大的区别,但仍觉得他们具有一些共同性,这些共同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带有文学新质的特点,丰富了当代文学的表现力。因此他们的写作不仅仅具有湖南的地域意义,也具有当代文学的整体意义。”聂茂说。
来自湘西的田耳与沈从文是同乡,这很容易让人们将他们俩连在一起来谈论,人们也自然而然地想从田耳的写作里寻找沈从文的影子。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乡土文化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与沈从文不同,田耳的小说中确有一种“人性的温情”,与他的温情相伴随的是一种冷峻,冷峻地面对现实困顿而展开精神的追问。田耳的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他的作品以温情的人文精神,淡定的叙事策略,深刻地反映了一群底层人物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命运挣扎。
谢宗玉是潇湘之地一只飞得特别高的散文之鹰。他把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对语言文字的艺术敏感都倾注到乡村,乡村是他生活和精神的气场,也是他执着表现的对象。无论是《田垅上的婴儿》,还是《遍地药香》,谢宗玉的散文总能直达读者心灵深处,把艺术感觉和审美情趣推到极致。
于怀岸是一个生活经验型作家,他的小说多写现实底层的生活,这与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他写得十分质朴和扎实,但在写实性的叙述中又透出一丝荒诞感,带着面对底层社会种种反常现象的疑惑。
沈念的小说和散文有着对日常生活独特细密的观察和与众不同的体验,带有某种呓语和旁白的气质。他是日常琐屑生活的旁观者,却又以一颗柔软敏感的心融入其中,表现出对人生的善意和悲悯。
“文学湘军五少将的作品具有明显的湘西风格特征,既有灵气四溢、山歌野调式的精妙语篇,又多大胆泼辣、血气方刚的激情文章。”聂茂说,“虽然表面看上去70后作家似乎是在各自为战,不事张扬,但是将其置于当代文学语境中,他们却又是一个厚积薄发的群体,只是这个群体在时代的逼仄下以不同的战斗姿态显现了其思考。”

“文学应该是以100年为一代的”
“与上世纪80年代文学黄金时期不一样,现在人们对于文学、特别是严肃文学的需求少了,越来越多的浅层读物,就能让人满足阅读的欲望。另一方面,受众都有一种路径依赖,就像一个人抽什么烟、喝什么酒、穿什么衣服,其实是认牌子。读者选择看什么书也是一样。作家越来越多,但严肃文学市场的蛋糕,却越来越小。”谈到当下的文学市场,马笑泉有些无奈。
70后作家向来被称为“夹缝中的一代”、“尴尬的一代”、“被遮蔽的一代”。他们位于60后与80后两个显赫的代际群体之间,一方面“打不过”长期把持着文坛话语权的有地位、资历和成就的50后与60后,一方面又面临着拥有广大读者市场、享受着商业红利的80后90后的冲击。
聂茂认为:“70后作家是不幸的,夹在两代人中间成为尴尬的一代,而他们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有幸亲眼见证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亲身经历了乡土文化的消逝,亲身体验到这种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相分离的痛苦、悲哀和挣扎。”
聂茂说,70后作家的成长恰好处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转折点上,他们的童年记忆以“文革”结束为起点,他们的青春期经历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之巨变,时代的动荡感造就了他们独特的精神气质,也使得他们的创作呈现沉稳多元的艺术风格。
聂茂说:“文学史绝对不以年龄和姿态作为价值坐标,因为两者都是暂时的、可疑的甚至是荒唐的刻度,只有作品质量才能衡量一个时代的文学和文化的兴衰浮沉。”
历史和现实已经为70后一代人提供了无比丰厚的精神滋养、无比宽阔的现实土壤和艺术想象力的庞大空间。作为文坛上越来越重要的创作群体,70后作家立足宏大理想和现代视野,尽可能将社会生活中的现代主义元素和故乡的本土化写作融合起来,就一定能写出全国性和世界性,被更多的人接受。
今年,70后作家徐则臣因凭借《北上》获得茅盾文学奖而被外界称为70后写作的振翅一搏,是70后作家这个群体的一次非常郑重的“自我证明”。
对此,马笑泉表示,没有人能代表70后作家,文学应该是以100年为一代的。后人来看我们,应该是把我们同陈忠实、韩少功、阿来、苏童等作家放在一代的。
拒绝标签化,也许,是70后作家的唯一标签。

对话
马笑泉:如果我们对世界达成共识,文学也就灭亡了
潇湘晨报:从《愤怒青年》到《银行档案》到《迷城》,是您创作的几个不同阶段,但您写的终究还是县城的故事。为什么始终会将写作的重心放在县城呢?
马笑泉:我在邵阳隆回县出生和成长,后来又在与家乡邻近的武冈、邵东两个县城中工作了八年。县城是与我的出生和成长息息相关的空间。70后作家一大特点就是城镇背景,城镇是我们叙述的原点,是我们的兴奋点。
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县城是至关重要之所在。县城一边是乡村一边是都市,一边是农业文明一边是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在县城交织、缠绕、激荡,表现得最为深切的,而且到现在仍未完结,还是现在进行时。所以我认为叙述县城就是叙述当今之中国,这与国家的发展战略是高度一致的。
从历史渊源来说,“百代都行秦政制”,秦朝创立的郡县制为我国古代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最有生气的、最鲜活的两大块,就是兰陵笑笑生笔下的清河县(《金瓶梅》)和施耐庵笔下的郓城县(《水浒传》),就是描写县城的市井生态。到了五四时期,因为鲁迅、沈从文他们这一批人,他们又把目光转到了乡土。上世纪80年代,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的兴起,包括韩少功,虽然他们出生在城市,但他们更出彩的作品也多是以乡土为主题的。之后的苏童、余华,他们的县城叙事,对70后作家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所以不仅我,还有很多同行,会自然而然地对县城展开叙述,这里面有文学传统和成长背景的双重作用。
潇湘晨报:有人说70后作家缺失了一份文学聚合力,在他们身上几乎很难找到如60后作家一样的文学一致性。因为他们从自我出发,又回到自我。对于这种论点,您怎么看?
马笑泉: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本能地抗拒批评家的这种武断概括。我始终觉得小说的起点是个人,是内心,通过内心出发,从见自我,到见众生,到见天地,通过共振与外界天地产生无限广阔的联系,这才是文学最大的聚合力,而不是对某种事物达成共识。共识这种东西,恰恰是小说家应该警惕的。如果我们对世界达成共识,文学也就灭亡了。文学存在的理由,就是它的独一性,独一性才构成世界的多样性。如果说我们有什么共识的话,就是对一致性的高度警惕。除此之外,我希望我们没有任何共识,一旦有了共识,我们70后作家就没有希望了。
潇湘晨报:70后作家曾引发文学界热烈关注,但这种热烈关注是由棉棉、卫慧等所谓“美女作家”引起的,您怎么看待风靡一时的70后美女作家?
马笑泉:这是70后作家的又一个不幸。70后作家一出场就是“美女作家”的出场,而美女作家,卫慧也好,棉棉也好,她们的写作各有各的特点,但她们的叙事艺术、文学修养、生活积累、情感深度,完全不能体现70后作家的真正高度。而且她们出道的时候,大部分70后作家还在成长之中,有的还在阅读之中,还没有开始写,凭什么她们就代表了70后作家呢?谁让她们代表了?现在“美女作家”们大多风流云散,但她们出道之初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人们对于70后作家的认知。所以70后作家后来的成长是很艰难的。也唯其艰难,所以成长得很坚实。后来像我们这些作家成长起来,也是一步一个脚印,一场一场战役打下来。我认为没人能来代表70后作家,我们连自己都代表不了,更不能代表别人。
其实“70后作家”这个标签只是一个方便言说,权宜之计。文学应该是以100年为一代的。后人来看我们,应该是把我们同陈忠实、韩少功、阿来、苏童等作家放在一代的。在这中间分50后、60后、00后是没有意义的。杜甫比李白小了那么多,但后人看他们,是同一代人。
潇湘晨报:你曾经说《迷城》是你青年写作的总结、中年写作的开端,在刚进入40岁就主动承认自己进入中年,是一种怎样的心态?
马笑泉:“青年写作”和“中年写作”不仅是一个生理年龄的问题,更是一个心理年龄的问题。有到老仍是“青年写作”者,比如李白,他一直就是处于青年写作的状态。也有步入创作不久就进入“中年写作”者,比如杜甫。大体而言,“青年写作”往往在某种强烈情绪的驱动下喷涌而出,呈现一种飞扬恣肆之态,更多地仰仗先天元气;而“中年写作”的节奏会慢下来,趋于舒缓、开阔、深沉,还包含了审慎和犹疑,后天的经验和思考的比重会逐步增加。二者皆能出佳作,只是面貌有异,气质有别。
对于我来讲,从“青年写作”到“中年写作”不止是年龄的增长,更多的是个人的个性、经历,使我的性格和写作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迷城》的创作和完成正好处于这一个阶段,作品所呈现的气质也是从青年时期的劲气奔涌转化为中年时期的舒缓深沉,这确实是一个告别式的总结,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开端。
潇湘晨报:从“青年写作”转为“中年写作”之后,现在40岁的你与当初15岁的你,看待你曾经生活的县城,有什么区别?
马笑泉:如果把写作比作绘画的话,以前我笔下的县城像是一个一个的大色块,色块之间互相激荡。如今我笔下的县城,更多的是点的互相浸染和线的交叉扭结。不同时期的色调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是因为我感受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是我并不悔少作。
潇湘晨报:在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中,和您同龄的徐则臣凭借长篇小说《北上》获奖,这是否将预示着70后作家进入新的阶段?
马笑泉:只要是凭实力获奖,都是好事。但作家最好不要老是惦记着奖项,那样只会干扰写作。我们更不能将奖项作为唯一的衡量指标,而应该扪心自问:有没有写出真正的杰作,有没有可能进入《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百年孤独》《树上的男爵》《失明症漫记》等等作品组成的经典谱系中。只有当出现这样的作品时,一代人的努力才不算落空。
来源:潇湘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