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重返小说的巨大矛盾之中|视频
时间:2019-10-28 13:32:41 热度:37.1℃ 作者:网络
当代文学史上,格非是个绕不过去的名字。继《望春风》之后,他又有新作《月落荒寺》。这是他2015年摘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四年间推出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相比同时代作家,格非的勤奋令人关注。
近日,在南京参加凤凰作者年会期间,格非接收了现代快报记者的专访。谈到《月落荒寺》这部描写当下知识分子精神迷惘的小说,格非表示,他是用平视的目光、带着尽可能理解他们的姿态去写作。他不是完全的批判,也包括对个人生活的反思。因为“书中人物的优点、缺点、欲望,以及在欲望中的挣扎,在相当程度上我也有。”
至于很多人反映的“小说好读”,格非表示认可,他甚至不介意读者将它当成通俗小说来读。
陈曦 / 文
《月落荒寺》的主人公叫林宜生,他是苏州人,在南京学习十年,然后北上,成为北京一所理工科大学的哲学教授。受益于市场经济和国学热,他在各地讲课,收入和地位跃升,名也有了,利也有了,却仍感到虚无,尤其是在妻子出轨白人汉学家派崔克,婚姻破裂,儿子不服管教后,他走到了生活的十字路口,感受到无力和彷徨。就在这时,一个叫做楚云的女子出现了。他被她的神秘所吸引,坠入了爱河。然而,有一天,当宜生服用了抗抑郁药入梦时,楚云消失不见了……
除了这条感情线,小说还写了林宜生和他的朋友们之间的故事。这个部分主要是描述不同的人,有知识分子、官员、生意人,还有艺术策展人,写他们的生存状况。
小说非常好读。格非提到,有朋友说花了四五个小时就读完了,然后问他,“林宜生最后跟谁结婚了”,其实他在小说里面已经埋下了伏笔,仔细的读者并不难发现。当记者表达了同样的阅读感受,并问他,介不介意新作被视为“通俗小说”时,格非表示,“我不介意。为什么要介意?”

《月落荒寺》
格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他说,作家有两种策略和手法,一种是把读者拒之千里之外,一种是跟读者保持直接的对话。随着时代的变化,作家和读者关系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想法,作家写作,首先要找到巨大的动力,觉得自己能写,有信心有激情去完成这个工作。如果读者读得很快,他喜欢读,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意外的。”
小说里的林宜生,和格非有着相似的经历和背景,都是在南方读书工作,后来去北方定居。为了不让读者将小说主人公当成作家本人,格非将林宜生的读书背景换成了南京。
但林宜生这个人,身上无疑有着当下知识分子的影子,包括格非自己。所以格非不是居高临下地审视笔下的人物,而是以平视的目光在描述他们,以尽可能理解这些人的姿态去写作,因为“他们身上的优点、缺点、欲望,以及欲望中的挣扎,在相当程度上我也有”。
2000年,格非离开读书、工作将近20年的华师大,调入清华大学。格非说,他是个不爱动窝的人,早就准备在上海扎根的,他妻子是地道的北京人,当时也已从北京调到上海,有了正式的工作,可家庭发生了变故,家中的老人需要照顾,他们又不得不匆匆忙忙调到北京。之所以选择清华,是王元化先生的推荐,王先生对他说:“你应该去不那么热闹的地方,清华就是这样的地方。”
来了以后,格非就发现北京对他太合适了,尤其是北方人大大咧咧的性格。“你在北京生活,你跟朋友之间,不会因为说错一句话,对方会生气,甚至跟你断交,这样的事情在北京从来不会发生的。可是在南方很多,南方人相对来说容易激动。我在上海生活的时候,这种事情发生了很多,有的时候,突然有一次见面,碰到一个人他就不理你了,转身就走了,你抓住他,问他为什么呀?噢,是因为他听到别人转述的一句话,这个话其实不是我说的,刮到他耳朵里。我也是这样的人,我的情绪也是比较容易激动的。”格非说,这是他作为一个南方人,才能体会到的北方人的品质,那就是情感的稳定和包容。
“当然如果你明天让我调回上海,我也会很高兴,没有问题。我在北京生活,那就充分享受北方的优点吧。”格非说。
20世纪90年代写完《欲望的旗帜》后,格非一直在考虑创作一部大的作品,历史跨度稍微长远些。希望能够用现代主义的方法来概括100多年间的历史,为此他做了大量的笔记。后来写不下去了,有很多原因。一方面中国社会在变化,80年代先锋文学的氛围已经不在了,另外他对现代主义这种方式也有些怀疑。还有一个他鲜少提及的原因,是他当时正读博士,其间又有了儿子。读博期间要写论文,没法写作;儿子还小,他只能整天推着他在校园里走。那时是有点苦闷和焦虑的。
直到2000年来到清华,孩子也上学了,各方面都安定下来。2003年,格非接受法国蓝色海岸协会邀请赴法,在那里开始了《人面桃花》的创作。从法国回来后,学校派他到韩国庆州做交换教授,他就在那座古老的城市里,用一年时间写完了《人面桃花》。这也是他后来摘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江南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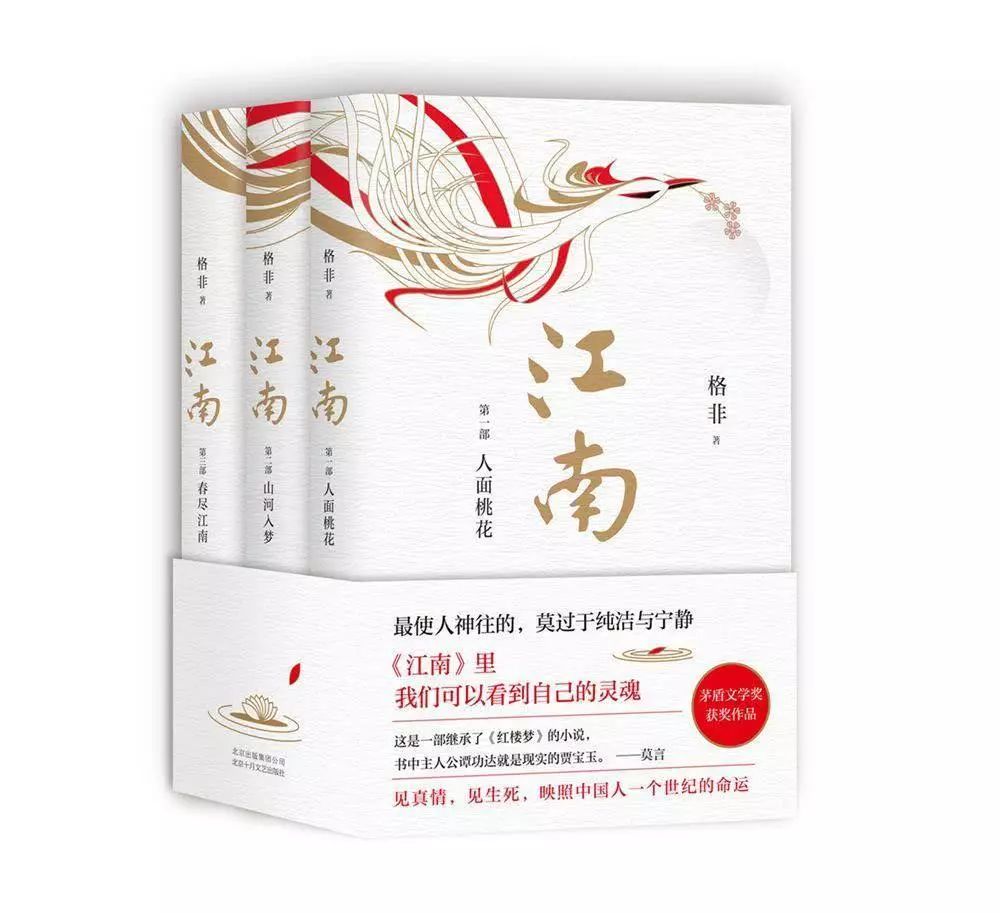
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
格非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评论界将这部小说视作先锋作家退场、转型的标志。但格非不这么看,他不认为《人面桃花》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他说,《人面桃花》与他80年代写的先锋小说之间是紧密关联的,当然里边有很大的变化。“步子可能跨得大了些,仅仅如此。”
《月落荒寺》是格非2015年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推出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在外界看来,相比同时代作家——苏童、余华未见新作,麦家十年出了一部,毕飞宇主要在讲“小说课”,格非近年来的勤奋令人关注。
对此,格非表示“不能这么看”,“因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工作节奏,有的人喜欢放个大招,几十年酝酿一部巨大的作品;有的作家觉得状态不好,就稍微停一停,我觉得这很重要,我当中也停了,十几年不写作。这都很正常。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格非觉得,他的这种写作节奏,很大程度上因为他是“业余写作”。他在高校当老师,人突然轻松下来就想写作。“可能是受工作习惯的刺激,好不容易把课上完了,学生的分数批出来,硕士博士把他们送走,有了间歇期,我就本能地会去写作,就觉得特别舒服。”
“但是对专业作家,或者对一个不受工作折磨的作家来说,他时间有的是,时间长了以后,他也觉得不着急了。我不行啊,如果这半年时间我把它放掉了,就要再等很长时间才会获得这个半年,这也是为什么我会特别在乎时间。”
当然,最主要的动力,还是写作带来的快乐。“没人让我写。相反,我的朋友、我的家人都希望我少写。我妻子就老是说,你能不能就不写了啊,你身体不是太好,教教书过过安静日子不很好吗?你老那么拼命写干什么?但是写作对我来说,这个快乐是不能剥夺的。”
格非在清华主要教授两门课,“小说叙事学”和“文学名作与写作训练”,后者是给本科生开的,学生很多。“每年讲的内容都不一样,不是说一门课我把它背下来,然后讲一辈子。每年都会有变化。”

在格非看来,教师是个严肃的职业。“我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学者,我就是一个教师”,而所谓“学者”这个部分,是为上课做的准备。他最近写的好些文学评论,都是他为了讲课,花几个月时间备课而写的。“如果我不是教师,我可能不会去花那么多力气,写那么多文章,去当一个什么学者。”
备课过程中,必然要去重读大量作品,重读各种理论,从整体上理解文学现象,理解作家,理解文学史的某些问题,让学生不至于觉得这个课“白听”了。
“你如果不去认真给学生讲课,你也不会那么认真地去读作品。你的竞争对手就是学生,一个班上有八九十个人,小的班也有五六十人,他们在也在读你读的作品,如果你的阅读还不如学生仔细,你怎么讲课?他们这么多人,一定会读出你读不出来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严肃的工作。大学里教书非常严肃。你讲课讲得好不好,学生眼里很清楚。”
“你如果十年前读过一本《罪与罚》,你怎么可能去给学生讲《罪与罚》?你起码得读两遍。这对创作有没有作用?当然也是有作用的。”格非说。

对 话
楚云易散,
世界上好的东西它都是不牢靠
读品:《月落荒寺》很好读,您写作的过程是不是也很顺畅?
▍格非:我跟别人有点不同,我是持续性的写作,写一个作品的时候,会有太多的东西放不进去。在写《隐身衣》的时候,有很多我想写的人物、场景、事件没有办法纳入到里面,但我也不能扔掉,所以就搁在那儿,慢慢的它就会有新的写作冲动。所以整个创作过程还算好吧,开笔的时候,一个礼拜有两次课,中间写作五天,不知不觉就把它写完,前后写了五六个月,那段时间我刚做完心脏手术,也不能太劳累,比较从容,也不太可能像过去那样熬夜,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读品:小说写了四个家庭、四对夫妻,身份是知识分子、官员、生意人、艺术策展人,基本代表了一个中间的精英阶层,他们物质充裕,精神生活上很享受,肉体也挺放纵,但内心比较空虚,您对他们的生活满意吗?是在反思些什么?
▍格非:也谈不上满意不满意。他们身上的优点、缺点,包括你讲到的欲望,以及欲望中的挣扎,在相当程度上我也有。所以我还是以平视的角度,带着尽可能理解这些人的姿态去写作,不是说完全地批判他们。就像王国维当年写《浣溪沙》,“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滚滚红尘那么多的人,但你又何尝不是他们的一部分?对文化也好,对一个群体也好,这种反思,也是对个人生活的一个反思。
读品:保姆老宋无意给狗喂了洋葱,结果狗死了,老宋被女主人赶走了,但老宋其实跟男主人德坤通奸。还有德坤家救狗比救人还尽力,最后还逼得人给狗下跪,这样的情节是想表达什么?
▍格非: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阶层关系小说里面带到一点,但不是这个小说重点描绘的部分。还有狗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不养狗,我在写作的时候也问过一些朋友,我说如果我要写这个的话,会不会触动那些养狗人的神经。所有的问题在今天都变得非常敏感,所以我在写这个部分的时候,实际上也非常小心。
读品:大家都知道您对《金瓶梅》的喜爱超过了《红楼梦》,楚云这个名字就是移植《金瓶梅》的,她很美,但结局很惨,让人感到美是那么脆弱。楚云这个人物代表什么?
▍格非:《金瓶梅》确实有一个楚云,这个人物出场的时候,小说就快结束了,她在来的路上,西门庆就死掉了。但是白居易也写过“楚云易散”这个典故,所以也不能说完全来自《金瓶梅》。
在今天,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美,实际上是“不美”,是非常做作的东西。真正美的东西,它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说到美,就会说到事物,如果放到人当中来看,就是在街上看到一个女孩很美,我会看她两眼,就觉得跟这个人有一种关系,因为这个美震动了你,不经你同意,它已经影响到你了。生活中会有一些东西强烈吸引你,为它付出情感,甚至我们很难用语言来描述它。这种东西我觉得很珍贵,它代表着某种激情。如果没有这种激情,生活是很枯燥的。这种东西在今天确实如你所说越来越脆弱,有些是转瞬即逝的,所谓“彩云易散琉璃脆”,确实如此。世界上好的东西它都是不牢靠。

《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
格非 著
作家出版社
读品:楚云的哥哥是黑社会,一个死而复活的死刑犯,这不由让人想起不久前云南孙小果案,《月落荒寺》其实两年前就差不多写好了,当时新闻还未发生。在新闻越来越超越小说家想象的今天,小说家为何还要写小说?小说的价值是什么?
▍格非:有人说新闻比文学更真实,我从来不这么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记录社会生活的方式,它有各自的规定性,不能混为一谈。首先,新闻诞生的时候,小说就已经诞生很长时间了。第二,新闻通常描述的是观念和道德,一个人杀了人,是非是很清楚的。文学要处理的,远比新闻更为复杂,它包含着非常多的观念,作家需要对这些意见和观念做一个综合。这是文学和新闻最大的不同。作家依附于新闻,通过新闻事件来刺激想象力,放弃了自己观察生活、思考生活的能力,放弃了小说家这个天然的权利,把自己新闻事件的再加工者,这是很荒谬的。
读品:小说应该干预现实吗?
▍格非:小说可以干预现实,问题是怎样干预?一个事件发生了,新闻会很快直截了当地表达看法。但小说不是这样,小说考虑的问题更加复杂。小说不光是对一时一地一事发言,它可能是对漫长历史的综合描述,所以小说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时空。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他的看法跟新闻差不多,这个女的通奸了、出轨了,他很生气,他想我的妻子要是这么做,那这个社会就乱套了。所以他本能地会对安娜很反感。但是《安娜•卡列尼娜》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托尔斯泰放弃了原来的看法,他写着写着发现自己爱上了安娜。安娜有自己的道理,他对她具有深刻的同情。他需要把现实的道德的自我,与过去保留他对象的一个自我,以及他想成为未来的一个对象物,形成一个综合。这样一来,在某种意义上,小说会反抗作者的固有观念。新闻跟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小说处在一种巨大的矛盾之中。很多小说家写到最后,走到了自己的道德和观念反面。这样的小说非常多。小说提供的是一个巨大的空间,促使我们对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的思考,这是小说的光辉所在。
很多悲观,
反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乐观
读品:《望春风》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吗?
▍格非:写《望春风》是因为老家的房子被拆了,乡村成为一片废墟,这对我的刺激非常大。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要把这些人写出来,不能让他这么消散了。我们老家原来是从河南迁居到这里,这个姓刘的村庄里面全是北方人,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乡下,突然赶上了这个巨变的时代,进了城,身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他们都垂垂老矣,已经极大地被边缘化了。可是他们的生命,在某个特殊的时间段里面是焕发出光彩、光亮的,他们也年轻过。你不能因为时代的变化,就把这段时间省略了。如果省略了,这些人怎么来交代自己的一生?他们大部分是不识字的农民,我觉得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有责任把他们的事情固定下来,或者说通过我的写作让他们活下来。这是当时比较强烈的一个冲动。
我不太愿意直接来描写我的经验,这是我一贯的立场。但是写《望春风》的时候比较投入,我也不管是不是我的经验。投入的程度太深了,时时刻刻处在一种激动当中,不是我要写这些人,是这些人会直接跳到我的笔下来,他们要求我把他们写进去,这种情感的浓度,是我以前写作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所以写的时候也是酣畅淋漓,没有觉得任何的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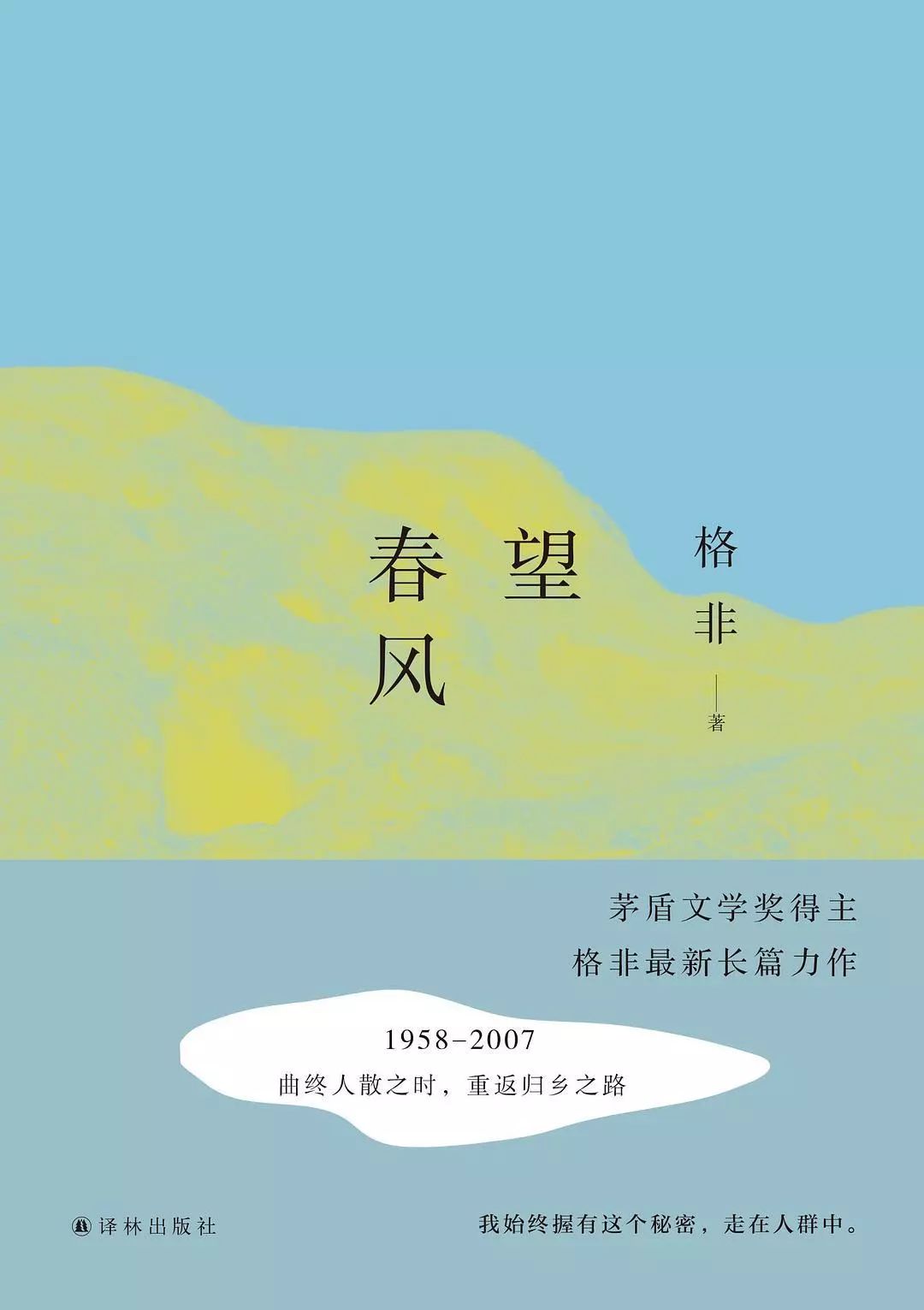
《望春风》
格非 著
译林出版社
读品:您说只有当某个事物到了它的终结之时,我们才有资格追述它的起始。而乡村生活对您个人来说是彻彻底底结束了,所以写了《望春风》。那么您在《望春风》里对乡村的书写是否得到充分的表达?以后还会再写乡村题材吗?
▍格非:英国的城市化进程19世纪中期就接近完成了。问题是,一个历史进程持续几百年,它到了中国才刚刚开始,或者说正在进行中。我们的观念认知,跟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之间有一个时间差。所以我也不是今天才意识到农业文明会慢慢消失,会被城市文明所取代。虽然这才是几年前的事情,可是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一种久远的记忆了。现在回家,都是住在城里的宾馆,乡下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你要再想写乡村,有非常大的难度。还有你的读者,也就是正在读书的这批人,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完全的乡村经验。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也一直在为小说的转型做准备,我也知道总有一天我写不了乡村。我实际上很早之前就想,会更多地去写城市。不是说乡村就不能写,或者说我以后完全不涉及乡村,而是需要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来认识乡村。
读品:您的小说是有明确是非观念的,但善良正义的一方总是吃苦、吃亏、失败的,而不那么善良的人却成功当道了。《望春风》里,德正早死,春琴晚景凄凉,为人阴狠的赵礼平却富贵得势。为什么这么写?
▍格非:这个问题也可以给卡夫卡、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加缪、鲁迅。所有的作家都是这么写的。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写?这是因为作家需要去描述个人生存和社会风尚、时代趋向、道德规定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小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本来就应该由小说家来承担。小说并不完全否定社会道德,但是它一定会在一种紧张关系当中去思考。不是所有的关系都是天然的,或者说它就一定是对的。比如文革时期的道德,对挣钱、对欲望,完全是鄙视的。但这个道德在今天已经被新的道德取代。道德也是不断在变化的。小说家就是在不断变化的道德风尚之间,进行比较深的思考,来重新构建关系,使得社会在不断的发展中,反思我们自身的生活。
读品:无论《春尽江南》《望春风》,还是《月落荒寺》,结尾都笼罩着悲伤的气氛。即便《望春风》的结尾,为“我”和春琴设置了一个美好的结局,但也明确告诉人们,他们相守的寺庙只是一座小小的孤岛,与时代的洪流背道而驰,他们的幸福终究是脆弱和虚妄的。为何小说常给人以虚无和绝望之感?
▍格非:我们往往把绝望和虚无看得太重了,这样就没有办法了解我们自己的生存。说到绝望和虚无,人最后都会被死亡战胜,最后孤独地死掉,这个结局肯定是不好的。那我们怎么来解释?比如说杜甫的诗歌,有很多激愤和伤感之词,那他为什么还要坚持他的看法?他永远会有牢骚,但同时意味着他对某种价值的坚守,这不完全是绝望。你坚持了你的价值,你的价值不为社会所容,你也会感到一种淡淡的满足。
萨特说过一句话,很多悲观的东西,反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乐观。一个人看透了世事,会获得一种新的境界。这种境界,不免是伤感的、悲剧性的,可是同时也会提供给你美的享受,给你真正的安宁。一个人如果对生活缺乏思考,就会随波逐流,就不可能获得安宁,永远在恐惧之中。生老病死,哪有那么容易摆脱?
读品:对《望春风》和《月落荒寺》这两部近作,您还满意吗?
▍格非:如果你觉得有信心把它拿出来给读者见面,你至少认为它还过得去。至于别人说好不好,这个我也不管,对得起自己良心就可以了。
对音乐的热情和喜爱超过了小说
读品:“月落荒寺”这个如此中国的名字,其实取自德彪西的曲子,“望春风”也是来自台湾歌曲。您的小说中对古典音乐也多有涉及,音乐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何影响?
格非:我听音乐是差不多三四十年了,这可能是我唯一的一个爱好。很多人会有误解,觉得我听音乐,好像是为了给写小说提供某种东西,其实压根就没有。我从来没带着某种功利性的目标和想法关注音乐,让它来帮助我写作,或是帮助我来理解历史、人生。纯粹的喜欢,有这个愿望浸透在其中。比如工作完了以后,每天回家,我就坐在沙发前听两个小时,有的时候会听四个小时。我一直觉得音乐的复杂神秘性,是小说远远不能比的。所以我一般不会把小说跟音乐相提并论。
读品:您觉得音乐比小说更高?
▍格非:当然要高很多很多。音乐跟我们情感的联系,那种直接性、瞬间性,带给我们的震撼,是小说不可比的。我们有很多心仪的小说家巨匠,也有很多音乐界的大师,但是我一般不会把他们放到一起,比较哪个更高。但是我对音乐的热情和喜爱超过小说,这是肯定的。
读品:这会对您的写作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吗?
▍格非:我觉得没有。说有影响都是在瞎胡扯。比如说有人从小说里读出了三重奏、四重奏结构,以昆德拉为例,这都不太对。音乐当中的对位关系、复调、曲式,跟小说完全是两回事。很多人不懂音乐,把音乐的结构跟小说结构来做一个比附,而且成为时髦。通常意义上说,巴赫是任何时候都能听的,不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巴赫从来不会错。还有一些音乐适合心情平静的时候,当你情绪激动的时候,可能不会去听肖邦的夜曲。音乐跟我们的关系,是一种更为直接的关系,听多了以后,会觉得它跟吃饭一样的,会有一种需要。
《人面桃花》不是跟80年代的切割
读品:格非、苏童、余华三人并举,被称为先锋文学的三驾马车。你们三个人当时面貌有何异同?后来的写作又出现了哪些分野?
▍格非:这也不是我所要去讨论的问题。我们作为作家,也不太会去考虑我跟余华、跟苏童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哥们一起过来的,有一种很自然的情感在里面。其实作家关注的总体的对象是一致的,这个对象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加之于我们的经验。我们怎么处理这个经验?对一般读者来说,他可能会觉得差别很大;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认为差别不大。他处理的经验、方式,我也心领神会。所以我也有一个观点,好作家是一群一群出现的,同行之间会获得很多启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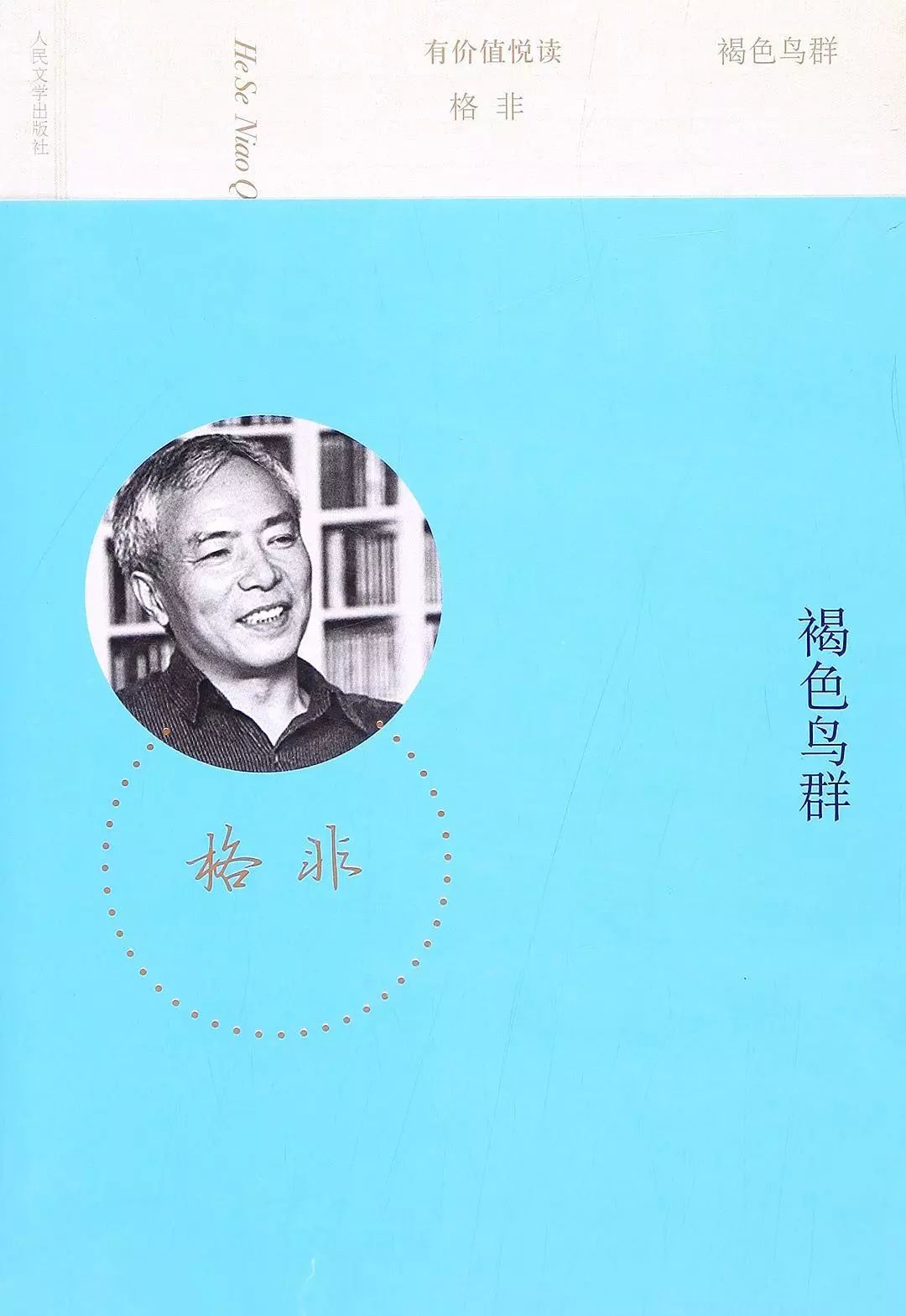
《褐色鸟群》
格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读品:《人面桃花》是一部带着先锋走进传统的作品,有人将它称为先锋退场的标志,您为何回归传统和写实?这种转向传统和写实,在您看来是一种必然吗?
▍格非:我的看法跟他们的都不一样。我觉得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写实主义,所谓现实主义也是一个神话。我不认为《人面桃花》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它跟我80年代写的所谓先锋小说之间,是有非常紧密关联的,不是说我把原来的东西扔掉,另起炉灶来写东西,当然里边有很大的变化,步子可能跨得大了一些,仅仅如此。当中也确实停了十多年,你要找回十多年前的感觉,你也找不着了呀。这个变化我也很难说得清楚,你的认识、心态,以及社会发生的巨变在你身上的投影,都能说明这个问题。一个年轻人激情飞扬写的东西,肯定跟到了中年不一样。但我不认为是跟八十年代切割。切割不掉的。里面很多东西不是纯粹现实主义的。文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那种界限分明的分类。这么一分的话,就没什么意思了。我从来不这么看。
读品:这段时间诺奖开奖、布克奖公布,大家对中国再出一个诺奖表现得非常渴望,您对当下的文学现状怎么看?
▍格非:莫言得奖的时候,我正好在伦敦;鲍勃·迪伦得奖的时候,我正好在纽约。都是第二天就有一个讲演。我当时就想,讲演当中可能会有人会问我对诺奖的看法。但最后情况截然相反,没有一个人向我这个中国作家问起莫言,也没有一个美国人问起鲍勃·迪伦,就像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一样,大家都在讨论文学,跟我交流对文学的看法。今年我觉得还好一些,尤其前几年,我们对诺贝尔奖,对在国际上获得承认,确实过于关注了。这个关注使得文学的生态变得很不正常。但这也是一个过程,随着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辨识度日益提高,这些问题会回归一个比较合理的范畴。获奖总是一个让人高兴的事情,但是也没有必要过于关注,还是让它变得正常。
读品:您对诺奖会有所期待吗?
▍格非:年轻的时候,对荣誉会有一种超过对生命的看重。艾略特说过一句话,荣誉和安宁不能共处一室。我觉得在今天,我对安宁,对我自身的生活不被打扰的这种想法,可能会超过你说的得奖、被大家热捧。
读品:有哪些您看好的青年作家?
▍格非:我经常看的不对。我自己有过惨痛的教训,就觉得某个人很看好他,突然就不对了;有些人你不并不怎么看好,几年以后把你吓一跳。有很多非常好的年轻作家,只不过是我们没有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青年作家年轻嘛,情绪容易变化,如果长久得不到社会的帮助,他确实没钱,他需要养家糊口,很多人就去挣钱、去打工去了。社会需要有对文学的奖励帮助制度,当然更重要的是,你得让他觉得他的作品很重要,有很多人看好它,能够提供这种动力。清华成立了文学创作中心,工作坊第一期就选了班宇、郭爽等人。衷心希望提供一个平台,让那些有潜力的作家,进入这个视野。
读品:最近有没有看一些作品,觉得还不错的?
▍格非:当然在看,班宇和双雪涛也给我推荐过,班宇给我开了一个很长的书单,我全部都买回来了。我喜欢那个理查德·耶茨,是由于张悦然的推荐。他是伟大的作家,也许是海明威、福柯之后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还有约翰·欧文也是他们推荐的,像这本《寡居的一年》,我带在路上看的。我想了解年轻作家在读什么书,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喜欢,他们创作的来源。我的书架里面好多的书,就是这种这样得来的,全是年轻人给我推荐。


格 非
原名刘勇,1964年生于江苏丹徒。1981年入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5年留校任教,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2001年调入清华大学。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欲望的旗帜》《江南三部曲》《隐身衣》《望春风》《雪隐鹭鸶》《文学的邀约》等。《隐身衣》2014年获鲁迅文学奖,《江南三部曲》2015年获茅盾文学奖。其作品被翻译成近20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
编辑:张垚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