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先锋作家的突围:知识分子为何总沦为边缘人?
时间:2019-11-21 02:23:27 热度:37.1℃ 作者:网络
你好啊,这是《Vista看天下》精选陪你的第128天。我们每天都会精选当期杂志文章免费给你看,本篇选自470期杂志,希望你能喜欢。
你可以扫下方二维码,直接订阅Vista看天下电子刊。还可以扫描文章中间的二维码,在Vista看天下App上免费阅读整本杂志——成为App的新用户,就可以领券免费阅读任意一期杂志了。
作家格非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小时候,他生活的村庄里有一位老人,待人和善,却总是说些大家听不懂的话。村里人都觉得这个老头是个疯子,格非也这么想。但他很好奇,老人到底在说什么。后来,格非去上海念大学,假期回家,有一天老头经过他的身边,对他说了一番话。格非听懂了,老头说的是英文。
很多年后,这件事被格非写进小说“江南三部曲”的第一部《人面桃花》中。格非曾说,假如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庄,也没有学过英文,这个经验就会一直存在记忆中,他也不可能了解这个老人的身世。
格非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于很多热爱文学与艺术的人来说,那个年代是浪漫的、自由的,也是不可重复的。格非经历了那个“对写作来说是最好的时代”。他的小说《迷舟》《褐色鸟群》曾是人们谈论现代主义文学时不可跳过的作品,他也和余华、马原、苏童等作家被称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
但八十年代也是短暂的。进入九十年代后,文学的环境发生了改变,彻夜不眠聊文学的日子悄然结束了,先锋文学也很快偃旗息鼓。
格非一度暂停了写作。他找不到写作的意义,不想写了。当时,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变。城市化扩张,他生长的乡村也变得面目全非。
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写完《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思考个体是如何被裹挟进时代的洪流,又是如何做出选择的。
今年9月,格非最新的长篇小说《月落荒寺》出版上市。
格非在新书自述中说,《月落荒寺》和《江南三部曲》《望春风》是有连续性的,都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持续的思考。
“我们生活中的每个人,由于这个时代的变化,我们都在重新定位自己,我们也在不断地调和或者说调整自己跟生活之间的关系。”

反乌托邦的乌托邦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格非就萌生了创作《江南三部曲》的念头。但直到2003年,他才动笔写第一部《人面桃花》。
当时,格非正在韩国南部的庆州做交换教授。那里的气候和格非的老家非常像,整天下雨,永远是湿漉漉的感觉。再加上庆州的古建保存完善,带着鲜活的历史感。格非呆在那儿,有种回到江南的感觉。
格非出生在江苏丹徒的一个小村庄里。对他来说,江南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也包含了历史文化的内涵和他的生活体验。
三部曲的故事从清末民初一直持续到2000年后,他用一个家族五代人的命运沉浮,串联起中国百年的历史变迁。书中的人物或多或少都和社会之间有种紧张感。格非觉得,离经叛道、处于边缘的人物,才能和他身处的时代拉开距离,做出反思。
如此庞大的构思,格非是出于时间性和空间性的两种考虑。
在时间性上,他想讨论那一百年对于中国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不断由历史片段组成的漫长的整体性的时间变化,我希望呈现一百年来连续性变化的轨迹。”
而从空间性来看,一个家族的几代人都在寻找某一种理想社会。“不断地呈现某种相似的历史场景,面对这种场景时人的作为以及情感的变化。”
在三部曲中,一个名为“花家舍”的地方不断出现。这是格非考察江南一带地方志时发现的地名,那里离格非的老家不远。三个故事都与花家舍有交叉。
《人面桃花》中,花家舍是个小渔村,也是革命的策源地;《山河入梦》中,花家舍成了县城,是文革前的时代样板;到了《春尽江南》,花家舍又成为经济发达地区的缩影。书中,花家舍代表了某种理想之地,隐喻不同时代的人们所追求的桃花源。
正因为如此,三部曲在台湾出版时,曾有朋友建议格非把名字叫作“乌托邦三部曲”。格非答应了,但很快又反悔。
相比于一些人认为三部曲在写乌托邦,格非更认可清华大学教授王中忱所说的“反乌托邦的乌托邦”的观点。
书中对于整个历史变化的思考,带有某种理想化的向往,但它并不等于乌托邦。格非认为,小说里写到的近代、现代的革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实践,跟乌托邦没什么大的关系”。

回不去的故乡
《人面桃花》中的花家舍,是一个修建在平缓山坡上的村庄。家家户户的房子都是一个模样,一律的粉墙黛瓦,一样的木门花窗,门前都有一个篱笆围成的庭院,宛如世外桃源。
书中的花家舍有格非外婆家的影子。那是江苏省扬中市的一个村庄,名为普济,三部曲中也出现了这个地名。
格非记得,那里河道密布,每家每户的格局完全一样,房子周围都有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门口一条小河穿过。河水四通八达,将整个村庄连在一起。
格非在乡村生活了16年,这构成了他人生第一段重要的社会经验。1981年,格非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初到上海的他并不适应,甚至对都市产生了排斥。那几年,格非把每次回家看成是“巨大的节日”。
“每个人都有对现实疏离的一部分,总觉得自己的生活在别的地方,美好的东西在失去的过去,总是想回到美好的生活情景当中去。”格非对本刊记者说,“这个故乡会成为我记忆中非常重要的枢纽,要不断地返回乡村的记忆。”
格非对这种“异乡感”并不陌生。他的母亲14岁从普济来到丹徒,作为外乡人,母亲一直有着不适应感。直到格非写作《人面桃花》时,母亲还常常念叨着要回到自己的老家。初到上海的格非,终于体会到母亲当年的感受。
距离那段日子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坐在本刊记者对面的格非今年55岁,头发斑白。他顺着回忆描述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村:“老家丹徒地处丘陵地带,地势起伏大。有时,你会看见一个人在远处的山坡上行走,头顶是漫天的白云。若是穿过大片的麦地,走到高处,向下俯瞰,附近的村庄都安安静静扎在树林里面。风刮过,植物的清新混杂着牲畜的粪味,是独属于乡村的味道。”
读大学时,格非带外地的同学到老家玩,有人感叹,丹徒有一种自然带来的伟大的孤独感。
只是,那时的格非还没有预料到,故乡也正酝酿巨变。
大学毕业后,格非每次回到家,都会发现那里正在一点点变化。
村子变脏了,河水变黑了,屋前屋后都是废矿泉水瓶和塑料垃圾。老房子也被推倒了,家家户户盖起新房,却没有整体的规划,哪个朝向的都有,走着走着就可能被一栋凸出来的房子堵住了去路。
又过了几年,那个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村庄,连同周围的五六个村庄全部被拆迁,变成了废墟。村民们也走了,奔赴城市。
“你会觉得突然你生存的根基没有了,那种感觉对我来说是非常刺激的。”一度,感到心痛的格非不愿意回家,“这些人祖祖辈辈扎根于乡村的那个东西没有了,他们就变成了真正的异乡人。大家会向往城市,不再把乡村作为一种千年不变的自己的家来守护。扎根在泥土之上的信仰开始根本动摇。”

开始写作小说《望春风》时,他采访了很多离开乡村的乡亲。
大家都感受到社会的变化,一种更大的力量推着社会往前走,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抵抗。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成了格非创作《望春风》的最大动力。
在《望春风》中,格非描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到2000年后中国乡村的变化,和身处其中的农民的个体命运。他在书中引用《诗经》里的“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感叹是什么导致这样的状况。
写《望春风》时,格非跟随母亲回了一趟老家。当时,村庄的废墟上长满了杂树、野草,甚至有了野兔。而如今,那里已经变成了商用飞机制造企业。
先打断你,休息一下。除了这篇上一期的文章,本期杂志还有其他精彩文章,不容错过——只要注册成为APP新用户,就可以免费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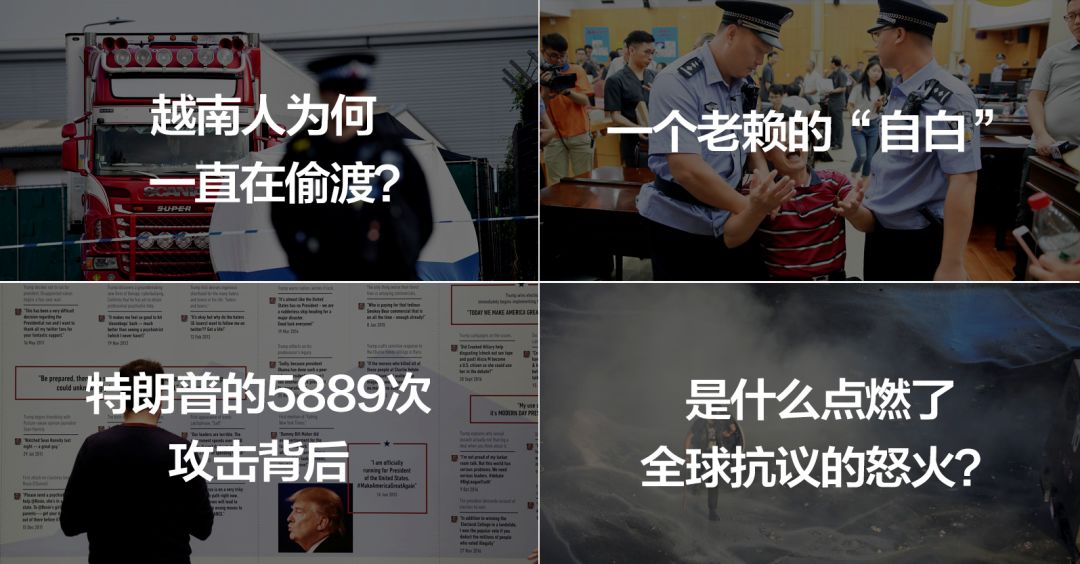
梦醒了
格非原名刘勇。时代的巨变曾经造就了他,也曾让他陷入迷茫。
1981年,16岁的他成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如果把当年的华东师大比作文化的中心,一点也不过分。那时,全国各地搞文学的年轻人,比如马原、余华,都以华东师大为重要据点之一。
有时,下午三四点钟,余华、马原背着包就出现在格非的宿舍楼下,喊他一起去参加文学活动。余华甚至在格非的宿舍里打地铺。马原更是有趣,半夜杀到格非宿舍,体型庞大的他睡不了地铺,格非只能把床铺让给他,自己睡地铺。
大家常常通宵达旦地聊天,话题围绕文学、哲学,以及各种不着边际的事情,聊到最后头痛欲裂。还有些夜晚,某个人起头唱歌,其他人也跟着唱,一晚上几乎把会唱的歌都唱了一遍。
那时,作家们对于文学的探索也总能得到读者热情的回应。
1986年秋末,马原到华东师大演讲。当他在一批追随者的簇拥下走向讲台时,格非看见站在门边的几个学生激动得直打哆嗦。社团联一位副主席在给马原倒开水的时候,竟然手忙脚乱地将茶杯盖盖到了热水瓶上。
格非也在那时开始写作,深受现代主义的影响。1986年,他发表了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和马原、余华、苏童等人成为了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
“那个年代是一个闲得发慌的年代。这些人都是搞文学的,经常凑到一块。那个年代完全是非功利的。”格非说,“对写作来说是最好的时代。”
但是,那段带着浪漫气息的岁月很快结束了。
随着市场化经济的形成,文学的环境也发生了改变。刊物、出版社相继进行市场化转型,新的读写关系形成了。
“这个状况给作家们带来非常大的恐慌,文学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原来理想主义的色彩慢慢消失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格非没有再进行写作。他甚至问过妻子,我将来要是不写小说了,你同意吗?妻子说完全可以理解。
“对那个社会的发展看不太清楚,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时代已经完全变了。那么在这个时代你写作的时候,你心里也完全清楚没有几个人能看。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写作是不是能够维持?”格非说。
格非遇到的困境不是个案。先锋文学的浪潮平静后,那些曾经迅猛涌现的文坛新人,有的转型,有的停笔。
马原曾把这形容为“做了一个梦,梦醒了就不写了”。1991年,马原撂下一句“小说已死”离开了文坛,成了导演、商人、教授,还和房地产商合作,开发楼盘。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两个时代交织变化中出现的一段空隙。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在这十年里经历了巨变。在格非看来,八十年代是一段过渡期,时间突然停在那里,但是它难以维系。当社会走入正常以后,它就结束了。
但格非还是继续写下去了。一直到《望春风》时,他觉得自己才看得比较清楚了。
他在接受《上海书评》采访时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思想的启蒙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开始了,但是真正大规模的城市化、乡村社会从根本上的瓦解,实际上是很晚近的事情,可能是在八十年代以后才发生的。这样来看,八十年代可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代的尾声,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两个时代之间泾渭分明。”
边缘人
今年9月,格非出版了新书《月落荒寺》,距离上一本小说《望春风》的问世已经过去三年了。
《月落荒寺》取自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同名作品。三年前,格非在一场中秋音乐会上产生了创作这部小说的想法,并在音乐会举办的七八个小时里构思好了框架,又花了五六个月的时间完成。
音乐似乎对格非的写作有一种奇妙的帮助。他曾在一篇散文里写道:“我总是凭借音乐来回忆一些往昔形象的片段,有些事情我原先以为没有经历过,可是某一种特定的旋律又会将我带到它的边缘。”
《月落荒寺》的主人公林宜生是在北京五道口某理工大学任教的老师,以他为中心,大学同学周德坤夫妇、好友李绍基夫妇、赵蓉蓉夫妇等八人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朋友圈。

格非的另一个身份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知识分子是他最熟悉的群体。他的小说常写知识分子,但大都是边缘人,在社会转型期处于无力而尴尬的状态,却在觥筹交错中热衷于谈论萨特、德彪西。
“《春尽江南》里,诗人谭端午沦为无所事事的废人。《月落荒寺》中,宜生名利兼收,仍解决不了生命的空虚。这些知识分子都不再是社会的主角,也无法通过劳动介入社会变革,他们要么迎合潮流,成为商业和政治的附庸,要么主动边缘化,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书评人宗城在评论文章中写道,“知识分子被三重落差压得喘不过气——理想和现实、过去和现在、欲望和萎靡。格非的小说里流露着沮丧。”
宗城将格非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处境与胡风在《时间开始了》里的自信、小说《青春之歌》热烈的知识分子相比,俨然换了人间——知识分子要处理的不再是天下问题,而是自我的矛盾,他们面对地位的落差,尝试克服内心的无力,但怎么克服呢?格非也没有明确的答案。
他一度把路径指向生活,暗示知识分子放下“大词”,关心生活中具体的美好,或者回归传统,抵御资本主义逻辑主导的商业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但这些解决方式失之于轻易,显得十分勉强,就像《月落荒寺》里缥缈的楚云,能给予知识分子一时慰藉,不能真正解决他们的精神危机。
宗城觉得格非在完成《江南三部曲》后,“他的创作也出现了一定瓶颈”。“一个是题材和人物关系的自我重复。一个是叙述语言的知识分子腔。格非写得最传神的人物是知识分子和充满欲望的女性,但在描绘其他人物时,就显得概念、泛泛。”
格非从华东师大毕业后就留校任教,后北上清华,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他的学生、作家吴虹飞形容他很热心,很好玩,说他有几句口头语:美好、漂亮。
有一次吴虹飞问他:“还有没有乌托邦?”他回答:“可能存在于日常中的一个个瞬间、灵感。比如说,我听了一段美妙的曲子,写了几句好的句子。再比如,在食堂排队打饭,突然发现自己的餐卡不能在这个食堂用,但饭已经打好了。怎么办?这时候一个女学生说,老师我来帮你。我想了很久,到底要不要把钱还给她?八块钱,她会不会觉得很幼稚?”
《月落荒寺》中女主角楚云的哥哥是黑帮头目,她的离奇身世引出了一段黑帮往事。不过,尽管格非用熟练的文字把故事写得很生动,但剥离掉叙事的技巧,这条支线仿佛是肥皂剧里的情节,有些牵强。小说也从探讨知识分子对于当代生活的迷惘,坠入到黑帮、复仇的俗世故事里。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格非也直言很多作家会重复表达某些主题。他提到托尔斯泰、海明威都在不断地关注同一个主题,所有的作品之间都建立了某种联系。
“我相信对我来说也是如此,但是我自己不太愿意去想这个问题。要想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写作就没有意义。”格非说,“我可能还觉得我要努力地拓展我的边界,我希望的是不断去投向新鲜的陌生的知识或者感知的领域。”
好了,文章读完了。如果觉得不错,记得分享到朋友圈哦。也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想法。
对了,提醒你,还是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全年更优惠噢。你也可以下载App,成为App的新用户,就可以免费看整本杂志了。杂志,一口气读完才过瘾。


